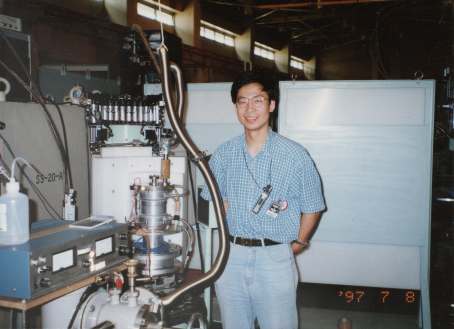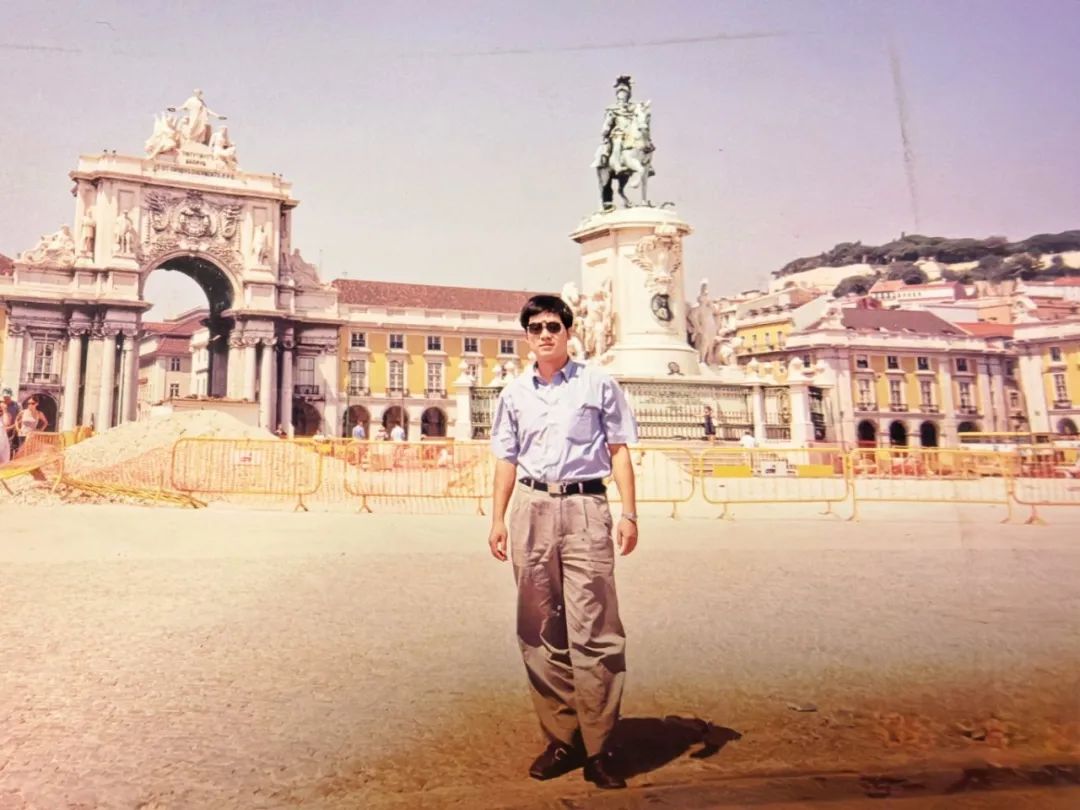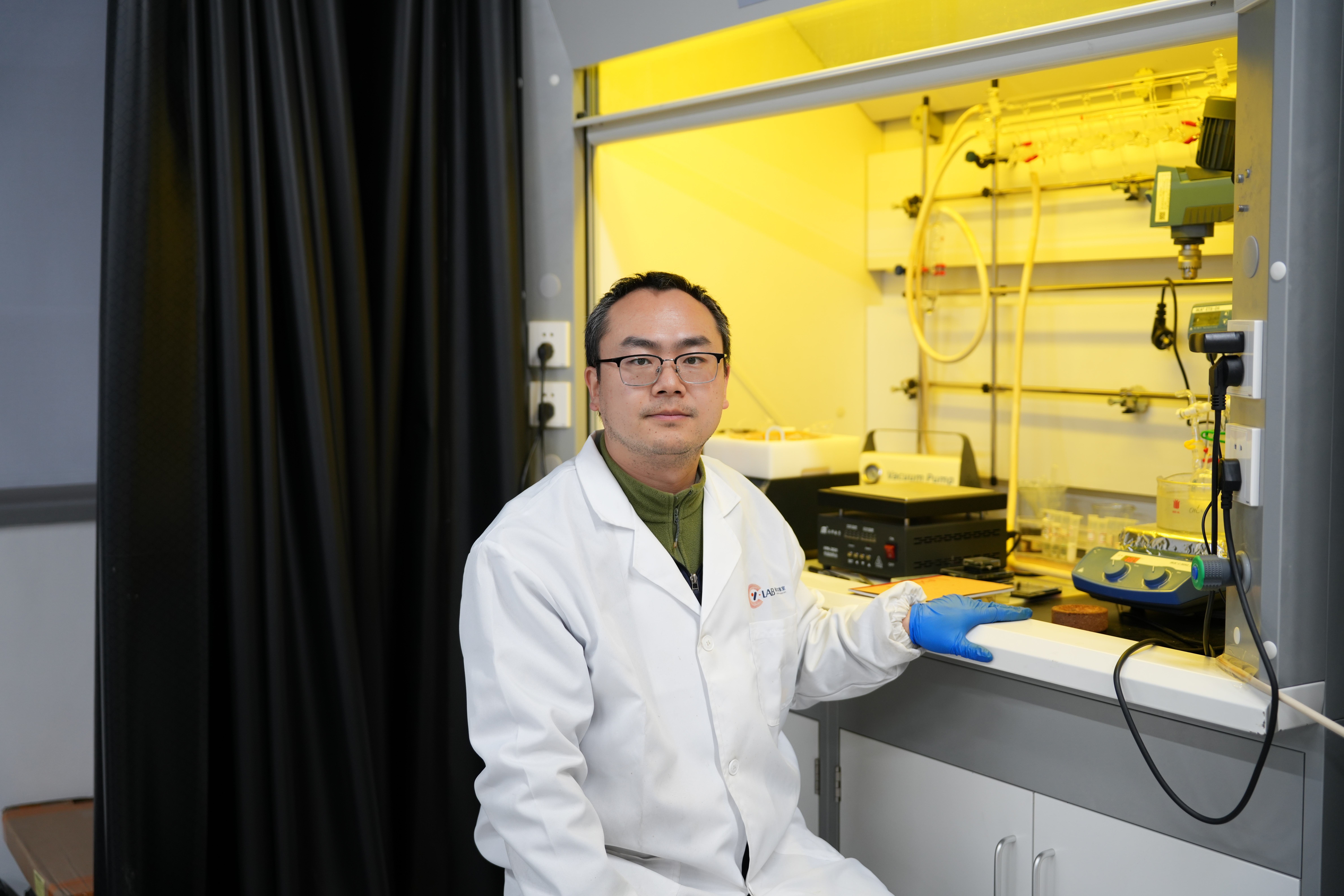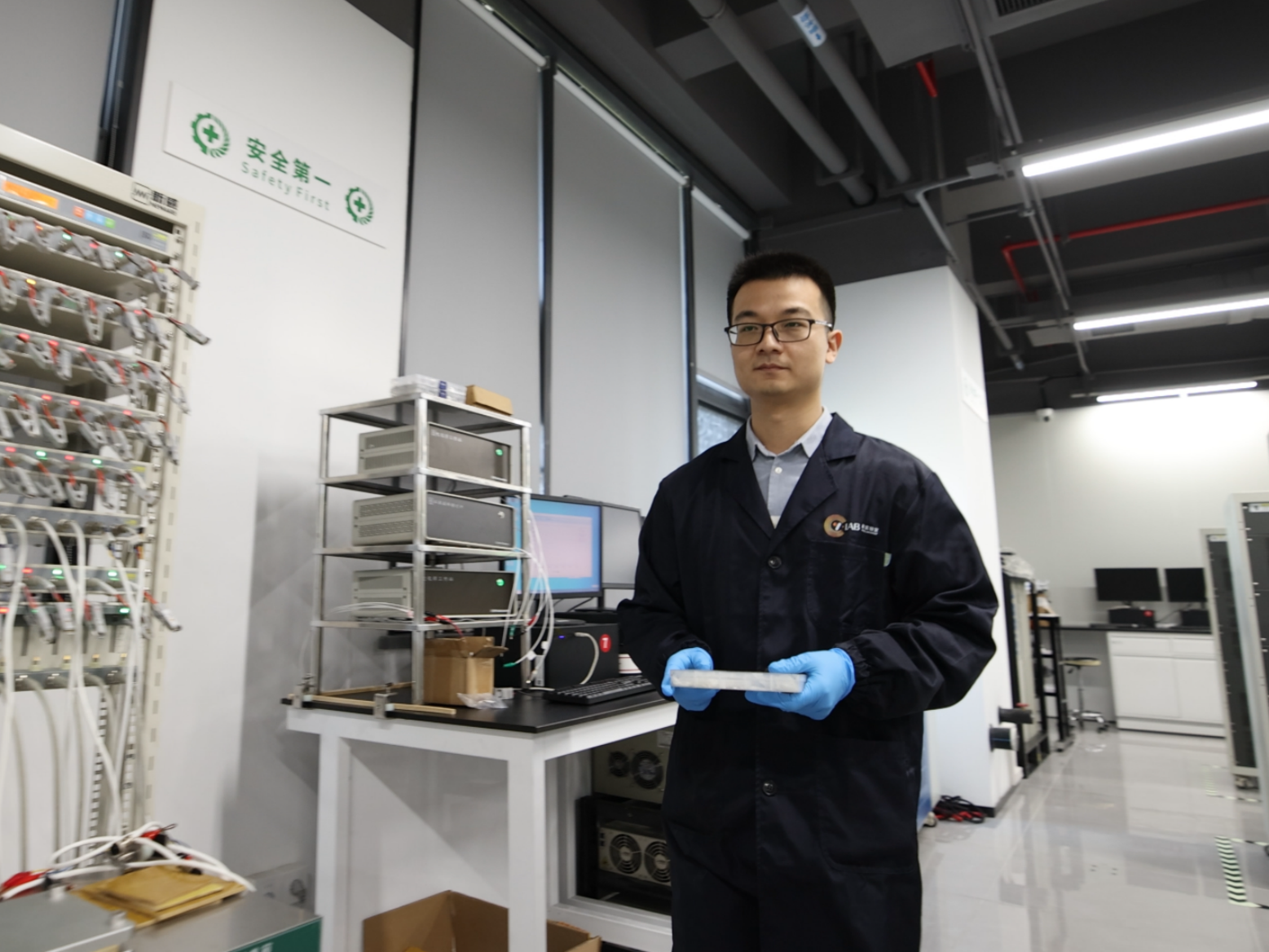31岁时的你,曾在做什么?
31岁的你,正在做什么?
尚未31岁的你,将要做什么?
反复提到31岁的原因是,甬江实验室共有科研和管理人员586位,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
在科研的漫长路途中,三十来岁往往是一个转折点——它既是青年时期的延续,也是迈向成熟科研生涯的起点。
有的人或许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的人或许正在探寻引领他们迈向科研新方向的路径。
我们不禁叩问:在这个被古人称为“而立”的年纪,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回应时代的召唤?
1942年,31岁的钱学森已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怀揣 “科学报国” 的赤子心,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埋下中国航天的第一颗火种;
1961年,31岁的屠呦呦刚完成卫生部为期2年半的中医培训,系统学习中医药理论,并不知道不久后自己将发现青蒿素的踪迹,为人类抗疟史掀开新篇;
1964年,31岁的陈景润蜷缩在中科院六平方米的宿舍里,在演草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哥德巴赫猜想的推导,那时的他尚未知晓,不久之后他的成果将让国际数学界为之震动,并以 “陈氏定理” 冠名……
当下,平均年龄31岁的Y-Labers,正沿着前辈的足迹,锚定“前瞻创新、从0到1、厚植产业、造福社会”,用行动去回答时代之问。
值此五四之际,我们邀请甬江实验室4位 “过来人”,讲述他们在31岁时的迷茫与突破,也邀请5位青年骨干,听听他们如何在当下书写属于自己的 “而立” 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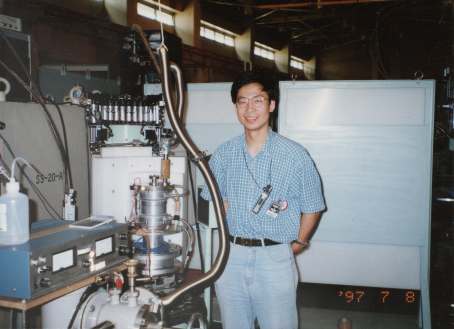
担任筑波大学文部教官助手期间进行实验
任晓兵 先进智能材料研究中心主任、上席研究员
31岁那年,任晓兵获日本筑波大学文部教官助手教职,并在Nature 杂志发表了一项重大成果。前一年,他拿到JSPS fellowship在筑波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他的合作导师——马氏体领域国际权威大塚和宏教授,给他出了一道六十余年来未解的难题:形状记忆合金的马氏体在“时效”后,从柔软塑性巨变为橡皮般的可回复弹性,但其微观组织和结构却毫无变化。这一现象挑战了材料科学和物理学的基本逻辑:宏观性能变化必然源于微观组织或结构的变化。任晓兵以苹果为例形象地解释了这种困惑:如果一个变味的苹果化学组成竟与新鲜苹果一模一样,所有人都会惊讶且无法理解。
抱着“有问题必有解”的信念,任晓兵另辟蹊径。他用逆向思维推测,一定存在一种现有常规检测手段无法捕捉的微观变化。经过逻辑推演,他提出“点缺陷短程有序对称性原理”,完美解释了这一奇特现象,并在数年后推广至铁电材料领域,发现巨电致应变效应。美国物理学会前会长Krumhansl称赞他是“马氏体地平线上跃出的新星”。
任晓兵将31岁左右的成就归结为“兴趣+信心”。他认为,兴趣是核动力,做科研时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或疑问,创新机遇便会自动找上门来;而好奇心叠加上克服困难后建立的自信,会形成正反馈,实现强大创造力。在具体科研战术层面,核心在于“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正如牛顿问“为什么苹果和所有物体都向下落而不是其他方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答案便呼之欲出。
人工智能风起云涌,我们如何做科研?任晓兵认为,AI在现有知识点的线性内插和外延能力上远超人类,但缺乏创造新知识体系和非线性联系的复杂思维能力。因此,我们应利用人类大脑的复杂思维能力,挑战突破现有知识体系的新原理或非线性关联等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这是AI难以取代的领域。同时,积极借助AI摆脱重复性劳作,腾出时间专注于高度创造性的工作。总之,AI时代对低端科研是重大的挑战,但对高度创新性科研是巨大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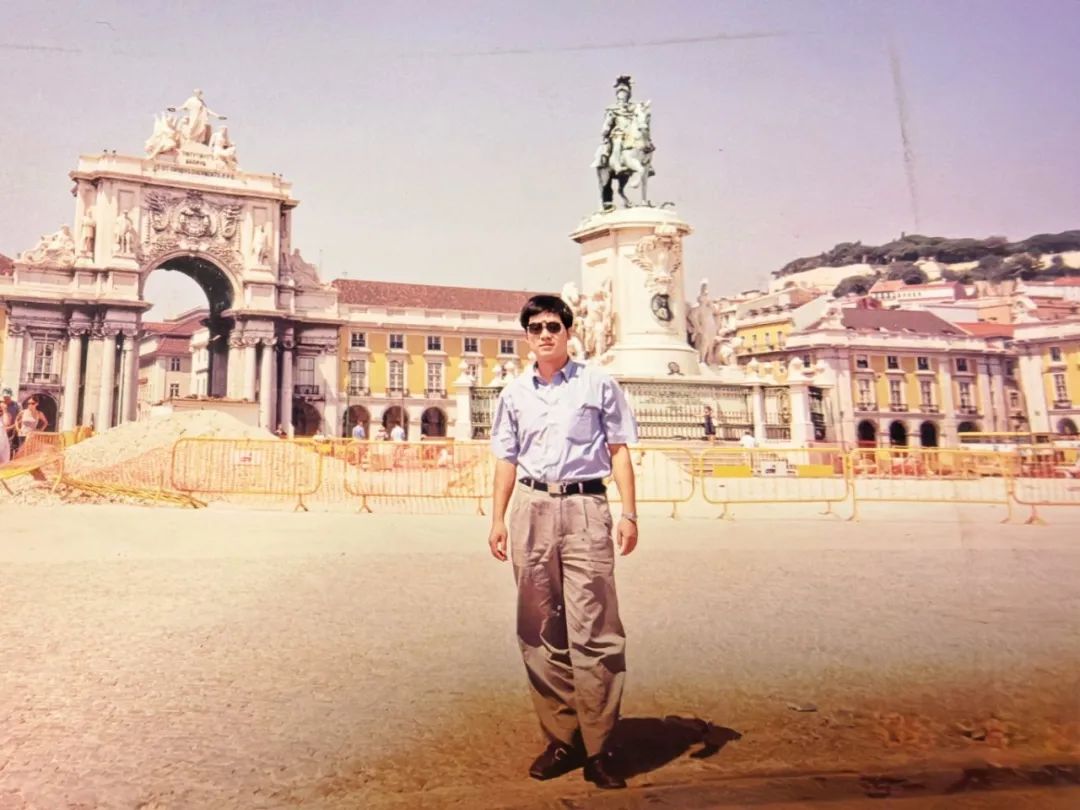
在葡萄牙留学时,游览里斯本奥古斯塔街凯旋门
陈克新 先进结构陶瓷创新中心主任
1999年,31岁的陈克新站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经历着科研生涯的重要转折。
当时的陈克新是清华大学材料系的一名年轻教师,即便在最高学府,科研条件也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实验设备常让他感到掣肘。尽管科研经费有限、仪器精度差距显著,但那代科研人总带着 “在艰苦中开拓” 的韧劲儿。
也是在这一年,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失利后,陈克新跟随当年的留学热潮,怀揣着对科研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渴望,踏上了赴欧洲求学之路。
在葡萄牙阿维罗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陈克新主导申请到了全校唯一的欧盟重点项目,并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重拾了科研信心。
这种对科研初心的“韧性”坚守,贯穿了他此后的学术生涯。加入甬江实验室担任先进结构陶瓷创新中心主任后,陈克新带领团队屡次突破陶瓷在室温下的拉伸压缩塑性,在Science 两度发表标志性成果,并有望逐步转化为重大工程领域的关键部件材料。
如今回望,这位科学家坦言:“如果遇见31岁的自己,最想说的还是要坚持热爱。”他想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最需要培养的是创新性思维、扎实广泛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团结合作精神。正如他经常引用的丁文江院士的对联,“醉心于事不记利,利随事成来;出世心作入世事,事随心气成”。在热爱与坚持中,世界终会看到每一位年轻科研人的光芒。

参加荷兰埃因霍温透射电子显微镜培训后,返程途径阿姆斯特丹在游艇码头留影
李昆 先进材料显微结构成像及表征中心主任、平台建设首席科学家
31岁那年,李昆博士毕业,加入新加坡材料研究与工程研究院(IMRE)。当时,研究院刚添置了全球最高分辨率商用电子显微镜,操作这台“高精尖”的任务落在他身上。这位年轻的助理研究员不满足于“会用”,更想深入了解其原理。于是,花数月逐字研读300多页说明书,成为少数真正吃透设备原理的专家。
三年后,李昆加入台积电与飞利浦合资的SSMC公司,负责筹建透射电镜实验室。在设备到位前,他被安排负责扫描电镜失效分析工作。这段看似平凡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首次有机会系统接触集成电路,亲眼看到芯片布局与构成,理解了其工作原理,为日后从事芯片失效分析打下基础。
随着半导体产业沿着摩尔定律演进,李昆加入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公司(现格罗方德),负责失效分析部门,亲历芯片从250纳米到32纳米制程的迭代飞跃。凭借深厚理论基础、实践经验和与时俱进的学习,他不仅能快速定位失效问题,更能深入分析工艺缺陷根源并提出改进方案,成为推动制程技术进步的关键人物。
之后,李昆重返学术界,在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主导建立世界级显微分析卓越中心,跨学科地应用最新电子显微分析技术,推动电子束敏感材料电子显微分析能力提升,奠定该校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
回顾一路走来,李昆感慨:科研如建金字塔,每块基石都决定最终高度。而自己每一步走来,都稳扎稳打,不在乎“浪费时间”,才有了一点点成绩。
眼下科研环境竞争激烈、瞬息万变,李昆提醒年轻人:切勿贪图短平快,莫被一时得失牵绊。务必扎实基础、拓展视野、触类旁通。否则,即便起步再快,也难以走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湖南大学期间,游览岳麓山清风峡中的爱晚亭
万青 功能材料与器件异构集成研究中心主任
31岁时,万青刚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成归来,回到国内加入湖南大学,成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 “芙蓉学者” 特聘教授。那是2007年初,国内高端科研人才还相对稀缺,科研平台建设也远不及现在完备,但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年轻学者有机会在新兴领域快速布局。
此前,万青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专注于氧化物半导体纳米线的基础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注意到日本学者细野秀雄关于非晶IGZO薄膜晶体管的研究——这种材料兼具透明特性与高电子迁移率,在柔性显示、可穿戴器件等领域有巨大应用潜力,但国内相关研究几乎空白。凭借科研直觉,他果断调整方向,成为国内最早开展IGZO薄膜晶体管研究的学者之一。
从零起步并不容易。当时实验室的设备条件有限,他带着学生自己搭建制备平台,反复调试工艺参数。2009年,万青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固态电解质为栅介质的IGZO双电层晶体管。2013年,万青团队成功发明世界首个IGZO神经形态晶体管,这种能模拟生物突触功能的器件,为类脑计算和柔性电子器件研究打开了新窗口。此后十年,他在 IGZO材料与器件领域持续深耕,推动相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探索。
回望31岁的选择,万青坦言:“科研路上总会有交叉路口,重要的是保持对新兴方向的敏感度,也要有勇气跳出已有的舒适区。” 他建议青年科研人员:“多花时间精读文献,在扎实的知识积累中培养学术判断力;敢于挑战常规,逆向思考‘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更要勇于尝试跨领域探索,有时候突破就藏在不同学科的交界处。”
如今,万青仍在前沿领域探索。在他看来,31岁的科研选择,或许正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突破的起点——那些敢于在空白处埋下第一颗种子的人,终将见证它在时光中生根发芽。
Y-Laber 青年,正当时

顾春阳 先进电驱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
“紧张而充实”,顾春阳这样概括现在自己的生活。聚焦让飞机、新能源飞行器的电推进系统更轻、更强、更“聪明”,顾春阳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出创新性的技术与方案,在可靠性约束下解决航空电驱高频损耗控制、磁性元件优化、散热与集成的关键技术,“好在甬江实验室为我们的科研提供了‘破局’的底气。实验室有国际领先的电力电子设备,依托丰富的产业化资源,加速了我们技术成果的转化与落地;开放协同的工作氛围,也有助于快速对接国内外专家学者。同时,在资源整合与科研管理方面,得到了职能部门的有力支持与高效保障。”
顾春阳希望,未来在颠覆性电力电子拓扑创新、智能容错控制技术和适航标准制定与产业落地三个方面实现突破。如果能实现这些,或许不久的未来,我们能看到搭载国产电推进系统的电动飞机翱翔天际,而宁波也有望成为全球航空电驱产业链的核心节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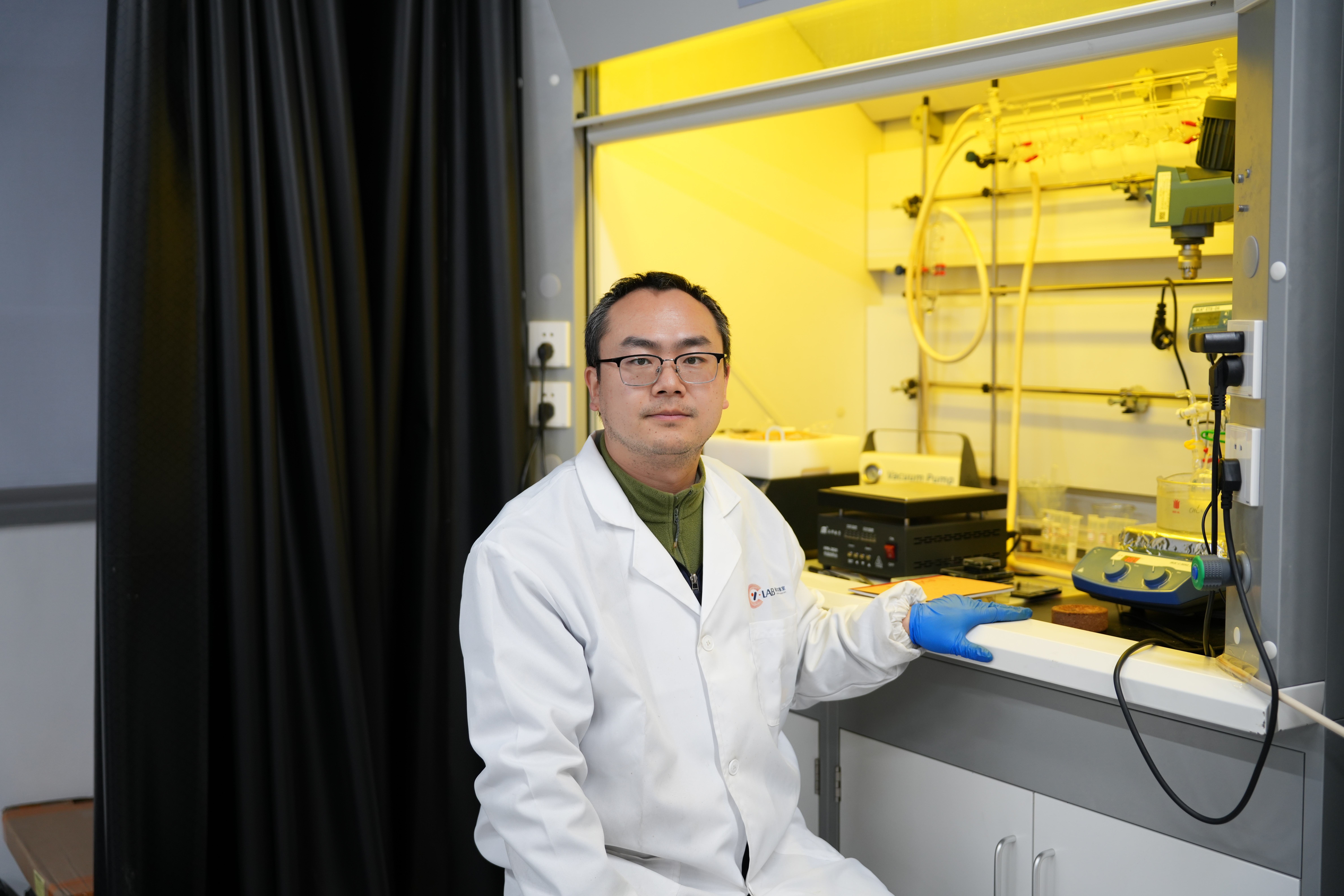
龙昱 激光微纳制造与测量研究组博士后
来到甬江实验后开展新课题和延续博士期间课题——多尺度的增材制造的材料、工艺和性能研究是龙昱目前工作的主要内容。两年的博士后工作即将结束,还有论文指标需要完成,下一步工作如何有效地开展,龙昱近期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一问题。“科研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出好的想法并变为现实,而不是一直跟随。在211、985院校和中科院系统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我体会到虽然甬江实验室很年轻,但给我这样的年轻人支持力度很大,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政策支持上,这是在其它地方所不能及的。”龙昱说,国内的科研竞争异常激烈,希望在甬江实验室能和大家一起成长,为国家、社会做出突破性科研成果。
谈及未来,他志存高远,希望在3D打印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领域能研发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设备和技术,发表有国际影响力的文章,让课题组成为这个领域被同行追随的领导者。“从2012年开始科研工作,至今10余年,一路上一直在跟随各位老师学习,接下来的路需要自己探索了。希望40不惑时,我能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做出自己的研究特色,仍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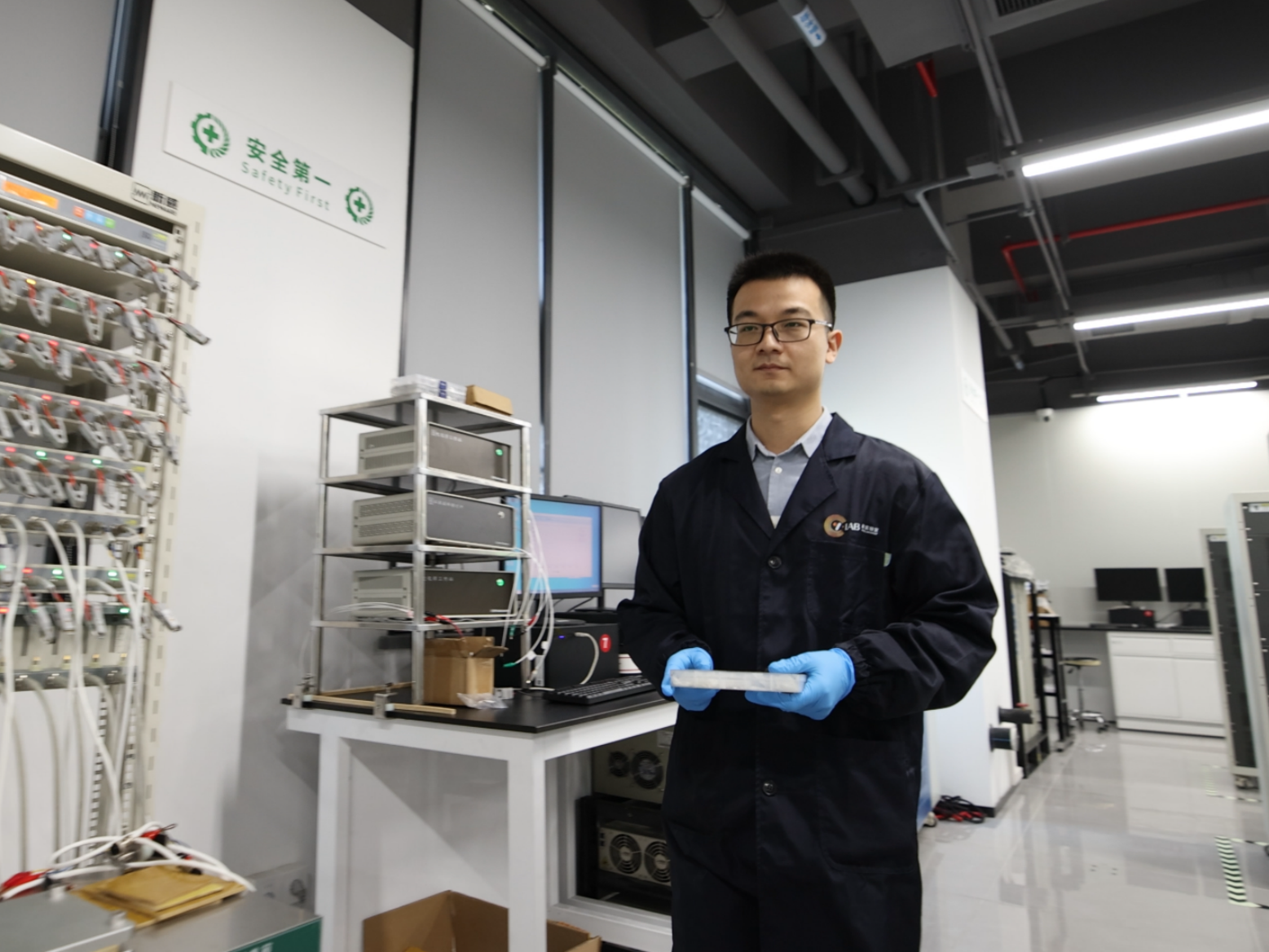
钱勇 多维度功能碳材料研究组博士后、副研究员
早8晚10,一周七天花一天时间陪陪家人,这是钱勇现在的生活状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硬碳材料与钠离子电池,钱勇走的是一条兼顾基础研究与工程转化的赛道。“现在主要面临研究深度与广度平衡的问题,目前精力主要放在团队建设上,个人没时间深挖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甬江实验室汇聚了多学科背景的人才,我会与他们多交流,拓宽自己的科研广度。此外,实验室在岗位配置与资金支持方面也给予了充分保障,有效助力项目团队的高效组建与稳定运行。”
钱勇希望未来10年能实现任何碳材料的定向合成,在知道用户的需求后,就能快速制备出所需的碳材料。着眼当下,他想踏踏实实干好每一天,不负光阴不负韶华。

刘艳茹 材料分析与检测中心技术组长
穿行在精密的仪器间,显示屏上的微观结构于刘艳茹而言不仅是图像,更是破解材料性能的关键线索。每天,她都专注于测试方案设计、实验流程优化、数据分析及技术培训,针对不同材料体系制定适配的测试策略,力求提升数据可靠性与结果解读深度。
工作的挑战藏在细节里。一方面,材料表征技术具有多学科复杂性,不同材料体系的微观结构与性能需求差异显著,需针对性设计测试方案并深化数据解读;另一方面,面对产业研发与科研创新的双重需求,既要保障测试服务的高效精准,又要推动新技术方法从理论到应用的转化,这对设备效能、技术储备及方法创新提出了持续挑战。
谈及未来,她的目标很明确:将显微表征等核心技术更加深入地应用到新能源、半导体、先进制造等前沿材料领域,不仅停留于表征,更能推动材料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之间的关联分析,为产业研发和重大科研项目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梁宏亮 科技发展部专员
从科研一线转向科技管理岗位的梁宏亮,每天在项目交流、资源协调、跨团队沟通中穿梭,这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的工作日常,充实中带着挑战,却也在磨合中愈发清晰方向。
“从前做实验,错了可以重来;现在做管理,每个任务都关联着多个团队的进度。” 他坦言,最开始分不清任务优先级,常被突发事务打乱节奏。但甬江实验室的包容氛围成了他成长的缓冲带:领导会耐心指导他拆解任务,同事们包容和理解彼此偶尔的疏漏,在实践中他也逐渐理解了科研管理 “服务者” 与 “协调者” 的双重角色。
展望未来,梁宏亮想搭建一套能真正提升创新效率的管理方法论。这个想法萌芽于日常与科研团队的沟通,他希望这套方法论不仅停留在纸面上,更能落地为可操作的工具,而甬江实验室的建设理念与创新氛围,正是支撑他探索的底气。
不止于此,梁宏亮心里还装着一个具体的小目标:主导一个从策划到落地的千万级科研项目。站在科研与管理的交叉路口,每一次会议上的思维碰撞、每一份流程优化方案,都是在为未来的科研管理方法论埋下基石,这正是他在甬江实验室写下的 “而立” 答卷。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31岁的刻度始终闪耀着开拓者的光芒。31岁既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一个需要勇气打破迷雾、用信念照亮前方的年纪。正如那些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科学家们,他们的“而立”之年,是积蓄、是探索、更是奋起。
以奋斗者为本,以做成事为要。甬江实验室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青春的名义承诺:我们将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每一次实验、每一份推导、每一项突破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而立”答卷。
青春是永远昂扬!
愿你我,无论几岁
都能赤诚不改
步履不停!